参孙选项:以色列计划如何利用核武器自杀?

“于是参孙把支撑房屋的两根中柱子拿来,靠在上面……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一同死。’于是他用力向柱子屈身,房屋就倒塌了。”
- (士师记 16:29-30)
1956年秋,一个非同寻常的早晨,以色列、法国和英国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三国入侵埃及”。然而,在炮火的轰鸣和舰队的移动背后,另一个计划正在暗中酝酿,一个比轰炸机场和占领苏伊士运河更危险的计划。
同一天,远离战场,一名以色列士兵拿起笔,在一个冰冷的金属物体上写下了一句简短的话语:“这不会再发生!”他指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纳粹迫害的时代。这名士兵是谁,这句话的内容是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在哪里写下了这句话。这句话写在了以色列第一颗原子弹上!
以色列之前的时代,第一个思想的诞生
恩斯特·戴维·伯格曼身材瘦削,面色苍白,烟瘾很大,一根烟也不放过。在他瘦弱的身躯背后,隐藏着以色列史上最危险项目之一的幕后主使:核计划。伯格曼出生于一个显赫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柏林的一位高级拉比,也是定居英国的俄裔犹太生物化学家哈伊姆·魏茨曼的密友。
1933年,纳粹政策开始压制犹太人在德国的存在,犹太学者几乎不可能在柏林找到工作。然而,由于父亲与魏茨曼的关系,伯格曼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了一个职位,并在那里继续他的原子分裂研究。在那里,他引起了丘吉尔二战前首席科学顾问切维尔勋爵的注意。
伯格曼曾为英国从事国防项目,尽管关于其工作性质的信息稀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并非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魏茨曼本人也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犹太复国主义项目密切相关。
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求魏茨曼派遣一名化学家前往巴勒斯坦,帮助生产一种用于对抗英国和阿拉伯人的高爆炸性物质。
当然,故事似乎很简单:魏茨曼除了拉比的儿子之外别无选择。伯格曼前往圣地,成为哈加纳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断晋升,最终在1939年被选中前往法国,与当时正在北非参与殖民冲突的法国科学家交流专业知识。
伯格曼亲身经历了纳粹统治,直到希特勒战败而告终。之后,他定居巴勒斯坦,并参与在特拉维夫南部建立了魏茨曼科学研究所。魏茨曼后来试图与奥本海默和曼哈顿计划团队建立合作关系,但尽管多次邀请他访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他的尝试仍以失败告终。
1948年“灾难日”(Nakba)之后,伯格曼的名字在以色列科学界声名鹊起。他被介绍为一位杰出的有机化学家,曾任魏茨曼研究所化学系主任,后成为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罕见的媒体露面中,他谈到以色列拥有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必要性,尤其是在阿拉伯国家的敌意以及以色列无法依赖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的情况下。
伯格曼曾告诉身边的人,该地区广阔的磷酸盐矿田铀矿储量有限。然而,1953年,他带领魏茨曼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了一种生产核反应堆所需重水的技术。
次年,他自豪地宣布以色列在“和平核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以色列还加入了“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并获得了第一座“用于和平目的”的核反应堆。
伯格曼并非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确实相信和平利用核能的可行性,但他也意识到,这个项目为制造核弹的动机提供了完美的掩护。他找到了一位比他更坚信以色列拥有核威慑力量必要性的政治和思想盟友:大卫·本-古里安,以及另一位年轻人西蒙·佩雷斯。佩雷斯三十岁时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并将原子能委员会置于他的直接监督之下。
三个男人,一个共同的梦想,以及对这个项目的坚定信念。他们只缺一样东西:一个盟友。
当法国打开反应堆大门时
以色列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生活在无尽噩梦的阴影之下。他认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威胁丝毫不亚于纳粹;事实上,他把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视为现代版的希特勒。
因此,他认为核威慑是防止“大屠杀”重演的唯一保证。他相信,阿拉伯人不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梦想,除非他们确信这个小国有能力在他们试图这样做时消灭他们。
伯格曼与本-古里安有着同样的信念,他也公开重申了这一点:“我坚信,以色列国需要自己的国防研究计划,这样我们才不会再成为被牵去宰杀的羔羊。”
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带领以色列走向核俱乐部门槛的盟友是法国,而不是美国,因为当时特拉维夫与华盛顿的关系并不处于最佳状态。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以色列的需求与法国的核威慑需求不谋而合,因为巴黎尚未获得美国、英国和苏联所拥有的核武器。
研制核弹的决定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争议。一些工党领导人认为,拥有核武器对这个新生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自杀威胁,但本-古里安和他的团队态度坚决。在法国,随着冷战的升级,以及尽管法国科学家在核裂变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法国仍被孤立于核武器计划之外,这场争论也同样激烈。
当法国人启动他们的核项目时,恩斯特·伯格曼的团队与他们并肩作战,该项目后来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殖民地进行了试验。法国人允许以色列人进入其秘密核社区的核心,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特权。据一些记载,以色列科学家在这些设施中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行动。
法国受益于以色列在科学计算方面的实力,这在当时至关重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些参与抵抗纳粹的法国人对以色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他们被欧洲犹太人的苦难所感动。
在这些同情以色列人甚至认同以色列的法国学者中,伯特兰·戈德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戈德史密斯是犹太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位成员联姻,进一步加深了他与以色列的联系。罗斯柴尔德家族曾为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助。20世纪50年代初,戈德史密斯作为伯格曼的客人前往被占领的耶路撒冷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并在那里结识了本-古里安,这次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他表示,法国人并没有“帮助”以色列人研制这种武器,而只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并补充道:“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拥有核武器是一项值得庆祝的成就,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是一种耻辱。”
这种伙伴关系很快开始结出硕果。1953年,魏茨曼研究所的团队成功研制出制造重水所需的离子装置,并设计出一种更有效的铀提取方法。这些发现被出售给法国,这笔交易为两国正式签署核研究合作协议铺平了道路。
1月,形势对特拉维夫有利,法国政府倒台,社会主义者居伊·摩勒出任总理。他对阿尔及利亚肆虐的革命比其前任更加强硬,因此对以色列的主要对手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也更加敌视。
通过武器交易、军事协议以及广泛的情报协作,法国与以色列关系迅速加强。此时,特拉维夫认为时机已到,需要向巴黎请求关键援助,以建立其军事核计划。
以色列意识到,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建造核弹项目的核心——化学后处理厂将无法实现。然而,他们面临两大障碍:一是资金问题,财政部长列维·埃什科尔称该项目的成本“疯狂”;二是安全问题,与保密有关。
最初,以色列考虑将反应堆建在里雄莱锡安的一座旧酿酒厂内,但测试表明该地点并不合适。最终,以色列决定将项目迁至贝尔谢巴附近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地区,正式将其定位为一家纺织厂。
资金从特拉维夫汇往巴黎,法国圣戈班公司的工程师们开始着手这个项目,他们对其巨大的野心感到惊讶。
计划中设定的最大热能容量为24兆瓦,但从冷却管道到废料处理设施等设计细节表明,该反应堆的实际运行能力是该容量的三倍。这意味着每年将生产超过22公斤的钚,足以制造四枚威力堪比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核弹,甚至超过当时法国反应堆本身的产量!
美国人……只是陌生人!
当然,以色列并没有向美国透露其核野心的真相,但命运让华盛顿很早就发现了以色列的核计划。在美苏对抗不断升级的初期,随着军备竞赛的全面展开,美国对苏联核计划的发展进行了痴迷的监视。直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U-2侦察机照相侦察小组出现,信息才逐渐匮乏。
这架飞机的首次飞行提供了苏联核技术进步的重要证据,但这还不够。华盛顿的目光还转向了巴勒斯坦沙漠,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以色列坚持隐瞒其军事能力感到愤怒,尤其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入侵之前。
突然,一架U-2侦察机在贝尔谢巴南部的一个以色列空军训练场发现了异常活跃的动静。尽管难以解读所有细节,但报告还是大量涌入白宫,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前一直关注的事情。
一个关键的视觉发现是迪莫纳郊外一片约12平方英里的荒芜区域被包围。起初,美国分析人士以为这是一个弹药试验场,但随后的图像揭示了重型机械、深层挖掘作业以及水泥正在涌入地下设施。华盛顿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纺织厂或军用仓库;这是一个核项目。
迪莫纳的建设引起了中情局的担忧,但奇怪的是,白宫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对中情局报告的回复也只是简短的“谢谢”和“这不会被发表吧?”
以色列很快得知了U-2侦察机的飞行情况,并开始每天使用密封卡车秘密清理残骸和废料。随着反应堆的建成,航拍照片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数年之后,美国人才得以确认以色列是否确实已进入武器生产阶段。
美国人试图寻找借口进入该地区,例如购买葡萄酒,中央情报局还派出了配备特殊镜头的自动相机的调查人员。
最初几年,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拍到好的照片,直到有人要求他们拍摄周围植被中钚或熔融金属的痕迹。以色列人对此的反应是种植高大的树木遮挡视线。到1959年底,华盛顿确信以色列正在“策划”其核计划,但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却选择掩耳盗铃。
这种宽容态度有很多解释。其中之一是美国人对犹太人的深切同情,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并非盟军的首要任务。盟军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德意志帝国,而不是解放灭绝营。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总统原子能顾问刘易斯·施特劳斯。他是一位犹太人,一直关注着迪莫纳报告,但从未发表任何评论或反对意见,似乎完全接受了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事实。1991年,他的妻子在去世前不久表示,尽管他极力保密,但他坚信以色列必须拥有核力量,以确保其在敌对环境中的生存。
或许和许多美国犹太人一样,施特劳斯认为“双重忠诚”的问题不应公开提出。他们担心对以色列的支持会被视为凌驾于对美国的忠诚之上,同时又担心阿拉伯人会察觉到这种同情,加剧他们对“犹太人阴谋”的恐惧,进而驱使他们疯狂地追求自己的核弹。
参孙传奇:从圣殿到迪莫纳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986年,在伦敦,物理学家兼《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彼得·霍纳姆(Peter Hounam)收到了一封神秘信件,信中自称曾参与以色列核项目。经过仔细审查,霍纳姆确认,发件人莫德凯·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确实是钚生产车间的一名技术员,信中携带着敏感信息。
通过多次会面,瓦努努向这位英国记者提供了精确的细节,不仅包括该项目的性质,还包括一张从地面上看都难以捉摸的绝密建筑图纸。
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时任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召集希伯来语媒体的编辑,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警告他们不要转载甚至提及这家英国报纸的报道。
此事曝光后,以色列随即对瓦努努展开追捕。当时,他正与一名美国游客在欧洲各地旅行,往返于英国和意大利之间。胡纳姆怀疑这名女子并非美国人,而是摩萨德特工,于是向瓦努努发出了警告,但瓦努努却让他放心。
不出所料,瓦努努突然失踪。调查锁定了“辛迪”——一位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女子,也是摩萨德特工的妻子。她引诱瓦努努与其发生关系,然后在罗马给他下药,随后摩萨德特工绑架了他,并将他带到了特拉维夫。
瓦努努因叛国罪和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处18年监禁。以色列的愤怒不仅源于该项目机密的泄露,也源于该项目对其政府所谓的“模糊威慑”国家战略的损害。
以色列热衷于报道其核计划,包括其核力量的谣言以及一些工人罹患的神秘疾病,但却不提供任何技术细节,官方也未予承认。这种“刻意含糊其辞”几乎已成为以色列政界精英和公众的共识。
但让我们回溯得更远。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起源于一场世俗运动,赫茨尔本人也是一位憎恨宗教的无神论者,但圣经神话和宗教术语的使用仍然是占领国叙事的基本支柱。宗教神话的动员力量超越了世俗的实用主义,尤其当一个国家建立之初就是为了用叙事和武器进行战斗时。
在这种叙事中,“参孙选项”的理念应运而生,这是以色列核支持者所倡导的一种自杀式核理论。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参孙,他被非利士人俘虏,被弄瞎双眼,并被献祭在加沙的大衮神庙。在圣经中,参孙呼求“以色列之主”赐予他最终的胜利,高呼“对抗我和我的非利士敌人”,并推搡神庙的柱子,直到柱子倒塌,压垮了他和他的对手。
在以色列国内,拥有核武器的想法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左翼人士的道德辩论。但政治多数派认为,为了防止二战中犹太人遭遇的重演,相互毁灭或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如果以色列的命运注定要灭亡,那么它的敌人也最好随之灭亡。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纳粹心理创伤和反阿拉伯观点,包括穆斯林和基督教的观点。
新移民试图塑造移民在荒芜土地上重新定居的形象,就像基布兹的理念一样,将农业劳动与苦难之后的安全感结合起来。然而,现实是,以色列建立在武器之上;为了确保“选民之国”的生存,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血。
因此,在法国的支持和美国的默许下,拥有核弹是以色列早期的战略目标。然而,以色列尚未需要援引参孙的神话来将自己与敌人一同毁灭;自1948年以来,它一直在使用常规手段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如今,加沙的大屠杀和饥荒在电视上以高清画质播出,而世界对此却毫不在意。看来,以色列如今更青睐的口号并非“对抗我和我的敌人”,而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圈子里反复出现的口号:“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新纳粹的受害者……我们将成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人。”
你的反应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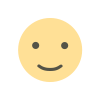 喜欢
0
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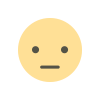 不喜欢
0
不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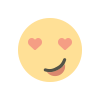 喜爱
0
喜爱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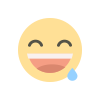 有趣
0
有趣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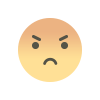 愤怒
0
愤怒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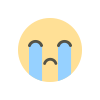 悲伤
0
悲伤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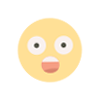 哇
0
哇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