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如何被推向战争并长期陷入其中?

无聊并非你日程安排中的空白,而是意义上的空虚。当你关掉尘世的喧嚣,发现充实你一天的事物却无法触及你的本质时,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事外;周围的事物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运转,而你却毫无理由地穿梭于它们之间。那一刻确实令人不安,但它也是通往自由的一扇小窗:奔跑中的停顿,以便让我们思考一个古老而痛苦的问题:什么值得我们为之牺牲生命?
在漫长的和平时期,或在漫长的战争间歇时期,这种感觉如同尘埃般在灵魂上积聚。只有通过一种有分量、有意义的行动才能平息——这种行动需要平衡我们所能做的和我们所感受到的挑战。如果挑战太轻,我们会感到无聊;如果挑战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就会精疲力竭、焦虑不安。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人们蜂拥而至,想要“做大事”;在那里,单调乏味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打破单调的欲望,有时是通过创造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有时——更危险的是——通过投入暴力的怀抱,这种暴力承诺着强度、确定性和归属感。
在我们能做的事情与我们所做事情的意义之间,在我们能做的事情与能让我们感受到活着的事物之间,这种差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每当我们的生活充斥着肤浅而缺乏目的的选择时,它就会出现。因此,无聊就成为了历史的伎俩,用以召唤那些被推迟的问题。那么,该怎么办?什么行动才能填补这种空虚,而什么行动又会加深这种空虚?
复杂的感觉
在詹姆斯·丹克特和约翰·伊斯特伍德合著的《我的脑袋快要裂开了:无聊心理学》一书中,他们试图将无聊定义为一种缺乏自主性和与周围人联系的感觉。他们认为,就像美一样,无聊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取悦一个人的事物可能让另一个人感到无聊。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医生将无聊定义为大脑皮层在面对琐碎刺激时活动减少。大脑会激活其他网络,导致人们为了寻求关注而做白日梦。这种状态就像我们经历的恶劣天气一样。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倾向于专注于精神事物,当我们的精神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时,我们就会感到不适。这类似于营养不良。无聊是一种信号,类似于营养不良时的饥饿感,它驱使我们去寻求这种专注。它是一种缺失某种事物的感觉,以及填补这种缺失的动力。这里有两种机制在起作用:未开发的精神潜能和欲望的困境。
马丁·海德格尔描述了不同程度的无聊:浅显的无聊,就像在火车晚点的车站感觉时间过得慢;短暂相遇的无聊,总是毫无意义地结束,人们在其中聊着天气、孩子和其他故事,这是与世界连接的时刻,是美好的瞬间,但在结束后却留下一种无聊的感觉;最后则是深度的无聊,每天的挣扎似乎毫无意义!一种可怕的空虚感,当我们无法创造令人满意的意义,我们的力量被耗尽,生活感觉就像站在深渊的边缘。列夫·托尔斯泰总结了这种困境,并称无聊是“对欲望的渴求”。
这种“无聊困境”在于,你想做某事,你有投入其中的渴望,但却看不到任何结果。无聊不同于沮丧。在沮丧时,我们找不到目标;而在无聊时,我们完全没有目标。我们想要它,却不知该如何定义它。我们充满痛苦,是因为一种我们不知该如何满足的需求。这并不是说我们尝试过却无法做到。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无聊是缺乏行动,不如说是缺乏方向。一天的任务可能被排得满满的,但我们却感觉自己游离于自我之外。让我们回归内心的,并非更加忙碌,而是在擅长的领域和挑战自身能力的领域之间取得健康平衡的行动。只有这样,时间才会流逝,感官才会被唤醒——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摆脱了无聊,而是因为我们触及了赋予工作价值的事物。
无聊:文明的缔造者与邪恶的起源
德国思想家兼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欲望、努力和渴望。幸福是满足一个欲望的暂时结果。一旦它得到满足,另一个欲望就会出现。在叔本华看来,我们的命运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受苦,要么是因为未能满足欲望的痛苦,要么是因为没有追求欲望的无聊。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合适的挑战能够平息长期的无聊:它能将注意力重新分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上,并为我们提供切实的目标检验。当这些条件长期无法实现时,诉诸任何承诺确定性和快速满足的现成框架的诱惑就会加剧。
所以叔本华说:“如果我们还有渴望和奋斗的目标,我们就会被认为是极其幸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这场将渴望转化为满足,再将满足转化为新的渴望的游戏。如果这种转变的速度很快,我们就称之为幸福;如果速度很慢,我们就称之为悲伤;而当它停滞不前时,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可怕的无聊——对生活充满了渴望,却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
这种感觉以各种形式陪伴着我们,记录了一段漫长、复杂而迷人的社会、哲学、文学和艺术史。如果我们的祖先满足于不去思考,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他们真的如此呢?他们满足于围坐在篝火旁,缺乏探索、创造和理解的动力,导致生命短暂而徒劳。然而,无聊如同痛苦,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告诉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人类正是以此开始构建文明的。
然而,同样的信号也可能被推到极限,以至于对“做大事”的渴望会增长到阻碍伦理反思的程度。正如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无聊正是各种邪恶的燃料。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摆脱快乐原则,忘记无聊的幽灵,我们就会走向一种更合乎伦理的生活方式,无聊也将不会再给我们带来痛苦。
伯特兰·罗素在其著作《征服幸福》中指出,战争、屠杀以及所有迫害都是逃避无聊的避难所,人类宁愿与邻里发生冲突,也不愿过着日常生活。他断言,我们比祖先更少感到无聊,但我们更害怕无聊。我们不认为无聊是人类自然命运的一部分,而是相信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寻求刺激来避免它。罗素还认为无聊是道德世界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对无聊的恐惧是人类一半罪孽的根源。深度无聊需要一场彻底的事件来恢复生活的意义,才能被彻底根除。正如约尔格·科斯特曼斯在其著作《无聊研究读本》中指出的那样,它可能是一场冲击,也可能是一场“振兴灵魂”的战争。这或许解释了他对比利时作家埃尔维斯·皮特斯小说的分析——这部小说讲述了一群青少年受无聊的驱使,独自走过一座通常行人不多的桥自娱自乐,但他们的出现和行动引起了骚乱,并让司机们措手不及。虽然离得很远,但他们的出现却让司机们感到困惑,其中一辆汽车撞上了桥,人们冲上前去救援,而这群青少年则拍了照,然后悄悄地撤离。
这群人早已习以为常。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聊感日益加深,为了克服这种无聊感,他们的暴力行为也变得更加复杂。他们发现了不同的兴趣爱好,有些兴趣与群体无关,而有些则积极参与。读者在故事中会发现,该群体当中的一个“孩子”正是提出这些想法并领导这群朋友的人,而且只有他真正具有暴力倾向,而其他人则参与其中以对抗无聊。但科斯特曼斯抓住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洞见:这些青少年并不实施暴力,甚至没有参与其中的感觉。他们只是引发和观察暴力。这是一种间接暴力,足以满足他们打破无聊的欲望。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上战争的火花之所以被点燃,就是因为有人仅仅出于无聊,就热衷于引发暴力以观察它并打破这种无聊?
第一次世界大战
2010年的一项学术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表明,无聊的确是古代历史上一些战争的动机。根据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说法,伊比利亚国王皮洛士的作战正是“为了不感到无聊”。
但现代社会更能揭示无聊的影响。它不再是贵族独有的感受,而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无聊,或者用作家迈克尔·霍华德的话来说,是一种“民主式”的无聊。它广泛存在,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宣战的决定,到厌倦了简单工作而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再到长期在战壕中等待、变得越来越残忍的士兵。
在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无聊似乎远非政治家和学者所能想象。然而,它却是普通民众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一个缺乏宏大宗教或文化叙事的社会中,战争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并成为了日常无聊的解药,能让人们重拾自主感。
这种情绪虽然无法精确衡量,但在艺术、诗歌、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却能有所体现。情绪本身依然神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再真实或重要。
根据这项研究,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以及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富裕阶层的兴起、富有创造力的工程师、工会、女权活动家、启蒙运动的兴起、工资上涨以及人们参与各种能带来幸福的活动,都将使人类更有能力达成和平协议。在日内瓦和海牙举行一系列和平会议和国际协议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内的一个国家试图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况下攫取另一个国家的财富,这似乎不合逻辑。
然而,城市化带来了疏离感和无聊感,普通民众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决策过程之外,无聊感便蔓延开来。在这样的情绪下,欧洲青年以压倒性的热情迎接了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政治家约翰·贝克尔写道:“号召进行一场伟大的世界大战意味着人们将不再伏案工作”,而他的同胞、画家弗朗茨·马尔克则将此视为“一场对抗欧洲灵魂中隐藏的、内在敌人的战争”。
因此,年轻的欧洲新兵加入进来,成为这场“伟大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是漫长无聊时光的终结。他们希望感受到力量,能够采取行动,或者至少是“光荣地死去”。
无聊的后续篇章
充满讽刺的是,驱使许多人走向战争的那种感觉,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漫长的无聊时光与恐惧交织在一起。在战壕里,个人决策寥寥无几,自主感也从未恢复。数月的等待,近900万人丧生,其余的人则经历了令人精疲力竭的徒劳。
然而,当那些在近十年后从前线归来的人们分享其战争经历时,从他们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正是他们的恐惧感。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在1928年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在1929年出版的《告别一切》等小说,传达了士兵之间深厚的友谊、牺牲精神以及许多其他美德。这些作品恢复了战争的浪漫主义,却忽略了战争的恐怖,而重申了当生活感到沉闷无意义时,战争可以成为一种解决方案的形象。
当社会缺乏一个具有切实道德内涵的统一故事时,承诺荣耀、团结和英雄主义的叙事就会泛滥成灾。在这里,暴力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还是一种尽快重塑自我和社群的手段。削弱这种浪漫主义魅力的是,存在着一些能够提供同样强度和目的感的现实替代方案:公共项目、实用知识、可见的团结,以及让年轻人扮演真实而非象征性角色的空间。
显然,那个年代的人们面临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作经历了显著的转变,从危险的、体力劳动转向轻松重复的工厂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作从危险的、高强度的劳动转向轻松重复的工厂工作:人们多年来从事简单的任务;长时间处于单调乏味的状态。随后的战争、维和任务——甚至“反恐战争”——也是如此:暴力事件爆发之间的长时间等待。
回顾科斯特曼斯的研究,我们发现,许多士兵并不认为战争是对抗无聊的冒险;他们是自愿参战,或者出于责任而参战。那些寻求战争来打破单调和无聊的人,他们的乐趣并非来自暴力本身,而是来自体验恐惧或获得赋予胜任意义的新技能,正如一位英国狙击手在其证词中所说的那样,他从精准的瞄准中获得的乐趣,比从夺取生命中获得的乐趣更大。
数字空间:战争不足以驱散无聊
在去年12月发表于《光谱》杂志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指出,无聊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情绪”。它是一种“没有品质的体验”,是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中隐藏的元素。因此,它突如其来,是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现象。它根植于历史,即使它难以被历史所认可。然而如今,随着现代科技解放了大量时间,它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
科技的确提供了过剩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它也承诺给我们无尽的娱乐。我们逃向屏幕;我们放松身心,浏览手机上的通知。我们看似舒适放松,但实际上,我们远离了自我。这种行为本身似乎毫无意义;无聊无处可逃。
战争也进入了我们的意识。研究人员追踪了不断看到战争的影响——这些战争始于广岛和长崎的首例原子弹爆炸,在当时,“绝对毁灭”的概念体现在了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有形图像中。但正如这些研究指出的那样,它让不幸的“他者”(无论是非欧洲人、殖民地还是边缘化群体)的持续悲剧变为既成事实,并且“极其无聊”。
在随后发生的战争中,我们被海量的数据和事件图像所包围。战争的瞬间影像将人们的苦难转化为视觉素材,得以传播并激发我们的情感。在这场洪流中,战争被分类——其中有些比其他更“有用”或者“重要”。这场洪流席卷了我们所有的媒体——电影、电视和社交媒体,从而导致我们对死亡和毁灭的图像麻木不仁。
当我们成为被动的消费者而不是主动的行动者时,一种无意义的状态在我们内心积聚,并将我们推向无聊。
媒体的作用和成就促成了战争的再现,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并将其融入算法,使之成为21世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娱乐、图像和消遣之中,战争图像与猫和名人的图像并列,与之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与其他内容一样,成为了无聊的根源。
因此,当我们融入一个冷漠的群体时,无意义感便会蔓延开来。重要的事件变成了失去意义的普通场景,痛苦图像的回响也消散在浩瀚的数字空间中。最终,我们共同见证了日常的平凡和悲剧:见证了朋友和名人分享照片的饭菜,见证了时尚和思想,见证了与我们同名以及我们子孙后代同名的孩子们的残破遗体,见证了各种屠杀与战争。见证是创造历史的必要行为,但我们却被一种充满内疚和无聊的文化所包围。无聊并非一种选择,但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切实可行的决定来应对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抗那些无情地奴役我们存在的东西。
数字洪流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娱乐,却未必赋予我们观看的意义。随着反复的观看,屏幕上的悲剧变得平淡无奇,失去了激发行动的能力。因此,或许治愈之道并非完全隔绝内容或沉浸其中,而是在于约束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设定特定剂量的日常或悲剧场景,然后通过实际参与或参与变革性运动来恢复我们的感知力,并赋予新闻以分量。
如果无聊有时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行动,那么治愈之道在于为正确的行动创造条件。或许我们必须在发展技能和不断以合理的方式挑战自我之间找到平衡。或许我们必须在社区和圈子中为自己找到有影响力的角色,机构和政府必须为年轻人体验意义和价值铺平道路,并致力于传递一种信息,以保护他们免受无聊的困扰,并避免利用他们对“做大事”的渴望而将他们推向毁灭性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聊并非宿命,而是对意义渴望的早期预警。问题不在于如何消除无聊,而在于怎样的意义值得被用来填补这份空虚?
你的反应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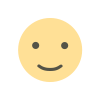 喜欢
0
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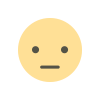 不喜欢
0
不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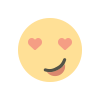 喜爱
0
喜爱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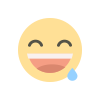 有趣
0
有趣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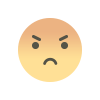 愤怒
0
愤怒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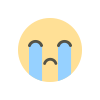 悲伤
0
悲伤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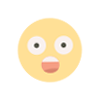 哇
0
哇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