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说|营收规模意外下滑,中航信发生了什么?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00696.HK)上半年营业收入38.95亿元,同比下降3.6%;归母净利润14.48亿元,同比增长5.9%。在国内航空市场全面复苏的背景下,航信业绩出现“营收下滑、利润上扬”的反差,引发市场关注。
具体来看,中航信过去贡献显著的系统集成板块收入大降38.5%,降幅位列各板块之首。尽管公司账上超过66亿元现金及税收优惠提供了一定缓冲,但随着出行需求回归常态,中航信的业绩却不及预期,公司经营压力正在浮现。
营收承压
航空需求整体回暖,但2025年中报显示中航信上半年营收仍同比下降3.6%;利润则在核心业务增长与坏账转回支撑下,上涨5.9%。
拆分来看,中航信主要业务板块呈现“冷热不均”。其中,航空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约23.13亿元,占总收入59.4%,同比增长2.1%;结算及清算服务收入约3.12亿元,同比增长12.4%;技术支持及产品收入为3.85亿元,同比大增30.4%,成为业绩亮点之一。这部分包括数字化零售平台、数据中台等产品化方案,在航司数字化转型加速背景下实现放量,提高了公司收入的弹性。
相形之下,系统集成板块大幅拖累业绩。上半年系统集成服务收入约4.18亿元,同比骤降38.5%。中航信指出该业务收入下滑,主要由于周期性项目建设进度放缓,以及部分业务用量在前期高基数上回落;数据网络服务收入下降约12.4%至1.90亿元。这些依赖项目交付和交易量驱动的板块回落,直接导致公司总营收承压。

从运营数据看,这种结构性分化与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公司中期公告披露,2025年上半年电子客票订座系统处理旅客约3.707亿人次,同比增长5.3%,其中中国境内航司订座量同比增长5.5%,但境外及地区航司订座量同比下降7.8%。同期国内民航市场总量已超过疫前水平:中国民航局发布的运输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约3.5亿人次,同比增长23.5%,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以上。但国际航线恢复相对滞后,航信境外航司业务量下滑反映出这一结构失衡,即国际订座量的不足对收入形成拖累。
在成本与利润方面,公司经营质量有所提升。2025年半年报显示,营业总成本约24.28亿元,同比下降4.2%,其中折旧摊销费用降低17.6%,系统集成项目成本同比减少52.1%。期间费用整体稳定,信用减值损益转回1.77亿元,这意味着此前计提的坏账准备部分转回,反映客户回款状况改善,提高了当期利润。财务数据显示,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约53.31亿元,计提坏账准备9.30亿元。尽管本期坏账冲回缓解了损益压力,但超过半年营收规模的应收账款绝对额仍需持续关注。
“财务结构显示出利润优于收入的韧性。”航空产业分析师周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航信上半年营收同比下滑3.6%,但归母净利逆势增长5.9%,靠的是航空信息服务和技术产品等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对冲了系统集成收入38.5%的降幅。他进一步分析称,上半年航信订座量增速放缓主要由于国际航段尚未完全恢复,但公司66亿元现金储备和1.77亿元坏账准备转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利润表现。“如果继续提升按旅客、按航段计费并叠加模块订阅的定价策略,并扩大高毛利的数据和结算产品供给,利润质量仍有望上行。”周衡说。
模式对标
中航信能够在本土市场构筑壁垒,一个关键原因是其深度嵌入了中国民航的行业规则和基础设施。中航信母公司为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国际航协(IATA)的资料显示,中航信运营着中国所有商业航空公司的中央订座和库存控制系统,为超过6500家机票销售代理提供订票和定价服务,相当于中国民航业的信息中枢。
这意味着国内航空公司和代理人高度依赖中航信的系统。中航信实际上还承担了类似IATA结算系统(BSP)在中国的角色——通过电子结算和清算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航司与代理人之间的票款清算与对账。这种“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赋予了航信极强的黏性和议价能力,使国外同行难以撼动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在技术演进和产品布局上,中航信与国际同业既有趋同也有差异。一方面,中航信积极参与全球航空业的新标准。半年报披露,上半年新增3家航司签署NDC直连协议,并推进ONE Order(订单一体化)标准落地,这与Amadeus等引领的行业方向一致。另一方面,中航信也开拓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场景:其APP离港系统已在182个境外或地区机场部署,用于保障中国航司航班离港(相当于将航信成熟的离港控制方案输出海外),而数字人民币支付在多个民航出行场景实现落地,区块链“航旅链”平台亦在上半年新增18家行业用户。这些创新领域是国际巨头较少涉及的。
与海外同类型公司相比,SITA等行业组织型企业侧重于机场和出入境流程的信息化改造。例如,SITA主要来自机场生物识别系统、行李追踪和空中联网等业务。可见在智慧机场、行李全流程跟踪等方面,中航信与SITA等各有布局。中航信背靠国内庞大的机场与航司客户资源,在推广新技术时具备更高的效率——截至2025年6月,航信的RFID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已推广至70余家机场,基于人脸识别的自助出行平台覆盖45家机场。
除了业务模式和技术路径,中航信与国际同业在财务与监管环境上也存在差异。中航信享受高新技术企业15%所得税优惠,并被认定为重点软件企业而按10%税率征税。2025年中期公告显示,公司于当年7月收到重点软件企业所得税退税约0.897亿元。这使其有效税率低于Amadeus、Sabre等通常20%—25%的企业税率,为净利润提供了一定支撑。资本结构方面,截至2025年6月末航信账上净现金超过60亿元;而Amadeus在2023年报中披露其年末净负债约21.1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60亿元),Sabre则因疫情冲击一直背负较高债务。
“航信的护城河在于其中枢式的平台群与本土监管环境的高度契合。”周衡表示,航信的业务模式并非单一软件产品,而是贯穿订票、值机、清算和支付风控的全链条服务,这使其在航司、代理人和机场3端都建立了深度黏性。“相比之下,Amadeus、Sabre等更多依赖标准化的每航段收费模式和局部IT方案,在业务纵深和生态控制力上略逊一筹。”周衡认为,随着NDC和ONE Order等新标准在国内落地,以及航信离港系统输出海外,公司的服务疆界正在外延。但长期来看,其增长仍取决于能否持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新的收入来源,并在国际化过程中保持对规则和安全的掌控。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00696.HK)上半年营业收入38.95亿元,同比下降3.6%;归母净利润14.48亿元,同比增长5.9%。在国内航空市场全面复苏的背景下,航信业绩出现“营收下滑、利润上扬”的反差,引发市场关注。
具体来看,中航信过去贡献显著的系统集成板块收入大降38.5%,降幅位列各板块之首。尽管公司账上超过66亿元现金及税收优惠提供了一定缓冲,但随着出行需求回归常态,中航信的业绩却不及预期,公司经营压力正在浮现。
营收承压
航空需求整体回暖,但2025年中报显示中航信上半年营收仍同比下降3.6%;利润则在核心业务增长与坏账转回支撑下,上涨5.9%。
拆分来看,中航信主要业务板块呈现“冷热不均”。其中,航空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约23.13亿元,占总收入59.4%,同比增长2.1%;结算及清算服务收入约3.12亿元,同比增长12.4%;技术支持及产品收入为3.85亿元,同比大增30.4%,成为业绩亮点之一。这部分包括数字化零售平台、数据中台等产品化方案,在航司数字化转型加速背景下实现放量,提高了公司收入的弹性。
相形之下,系统集成板块大幅拖累业绩。上半年系统集成服务收入约4.18亿元,同比骤降38.5%。中航信指出该业务收入下滑,主要由于周期性项目建设进度放缓,以及部分业务用量在前期高基数上回落;数据网络服务收入下降约12.4%至1.90亿元。这些依赖项目交付和交易量驱动的板块回落,直接导致公司总营收承压。

从运营数据看,这种结构性分化与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公司中期公告披露,2025年上半年电子客票订座系统处理旅客约3.707亿人次,同比增长5.3%,其中中国境内航司订座量同比增长5.5%,但境外及地区航司订座量同比下降7.8%。同期国内民航市场总量已超过疫前水平:中国民航局发布的运输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约3.5亿人次,同比增长23.5%,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以上。但国际航线恢复相对滞后,航信境外航司业务量下滑反映出这一结构失衡,即国际订座量的不足对收入形成拖累。
在成本与利润方面,公司经营质量有所提升。2025年半年报显示,营业总成本约24.28亿元,同比下降4.2%,其中折旧摊销费用降低17.6%,系统集成项目成本同比减少52.1%。期间费用整体稳定,信用减值损益转回1.77亿元,这意味着此前计提的坏账准备部分转回,反映客户回款状况改善,提高了当期利润。财务数据显示,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约53.31亿元,计提坏账准备9.30亿元。尽管本期坏账冲回缓解了损益压力,但超过半年营收规模的应收账款绝对额仍需持续关注。
“财务结构显示出利润优于收入的韧性。”航空产业分析师周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航信上半年营收同比下滑3.6%,但归母净利逆势增长5.9%,靠的是航空信息服务和技术产品等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对冲了系统集成收入38.5%的降幅。他进一步分析称,上半年航信订座量增速放缓主要由于国际航段尚未完全恢复,但公司66亿元现金储备和1.77亿元坏账准备转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利润表现。“如果继续提升按旅客、按航段计费并叠加模块订阅的定价策略,并扩大高毛利的数据和结算产品供给,利润质量仍有望上行。”周衡说。
模式对标
中航信能够在本土市场构筑壁垒,一个关键原因是其深度嵌入了中国民航的行业规则和基础设施。中航信母公司为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国际航协(IATA)的资料显示,中航信运营着中国所有商业航空公司的中央订座和库存控制系统,为超过6500家机票销售代理提供订票和定价服务,相当于中国民航业的信息中枢。
这意味着国内航空公司和代理人高度依赖中航信的系统。中航信实际上还承担了类似IATA结算系统(BSP)在中国的角色——通过电子结算和清算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航司与代理人之间的票款清算与对账。这种“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赋予了航信极强的黏性和议价能力,使国外同行难以撼动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在技术演进和产品布局上,中航信与国际同业既有趋同也有差异。一方面,中航信积极参与全球航空业的新标准。半年报披露,上半年新增3家航司签署NDC直连协议,并推进ONE Order(订单一体化)标准落地,这与Amadeus等引领的行业方向一致。另一方面,中航信也开拓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场景:其APP离港系统已在182个境外或地区机场部署,用于保障中国航司航班离港(相当于将航信成熟的离港控制方案输出海外),而数字人民币支付在多个民航出行场景实现落地,区块链“航旅链”平台亦在上半年新增18家行业用户。这些创新领域是国际巨头较少涉及的。
与海外同类型公司相比,SITA等行业组织型企业侧重于机场和出入境流程的信息化改造。例如,SITA主要来自机场生物识别系统、行李追踪和空中联网等业务。可见在智慧机场、行李全流程跟踪等方面,中航信与SITA等各有布局。中航信背靠国内庞大的机场与航司客户资源,在推广新技术时具备更高的效率——截至2025年6月,航信的RFID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已推广至70余家机场,基于人脸识别的自助出行平台覆盖45家机场。
除了业务模式和技术路径,中航信与国际同业在财务与监管环境上也存在差异。中航信享受高新技术企业15%所得税优惠,并被认定为重点软件企业而按10%税率征税。2025年中期公告显示,公司于当年7月收到重点软件企业所得税退税约0.897亿元。这使其有效税率低于Amadeus、Sabre等通常20%—25%的企业税率,为净利润提供了一定支撑。资本结构方面,截至2025年6月末航信账上净现金超过60亿元;而Amadeus在2023年报中披露其年末净负债约21.1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60亿元),Sabre则因疫情冲击一直背负较高债务。
“航信的护城河在于其中枢式的平台群与本土监管环境的高度契合。”周衡表示,航信的业务模式并非单一软件产品,而是贯穿订票、值机、清算和支付风控的全链条服务,这使其在航司、代理人和机场3端都建立了深度黏性。“相比之下,Amadeus、Sabre等更多依赖标准化的每航段收费模式和局部IT方案,在业务纵深和生态控制力上略逊一筹。”周衡认为,随着NDC和ONE Order等新标准在国内落地,以及航信离港系统输出海外,公司的服务疆界正在外延。但长期来看,其增长仍取决于能否持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新的收入来源,并在国际化过程中保持对规则和安全的掌控。
你的反应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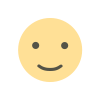 喜欢
0
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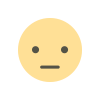 不喜欢
0
不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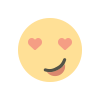 喜爱
0
喜爱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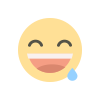 有趣
0
有趣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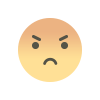 愤怒
0
愤怒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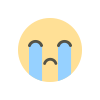 悲伤
0
悲伤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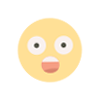 哇
0
哇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