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日本决定残酷入侵邻国的原因

1937年12月13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帝国陆军刚刚攻占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当时,日本大元帅松井石根下令,他的胜利之师将南京彻底摧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日本军队以最残酷的方式,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指挥官的命令。
其结果是一场彻底的悲剧: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统计,死亡人数在10万至30万人之间,后者是北京采用的官方数字,此外还有数万起强奸妇女的案件,以及该市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毁,周边城镇被烧毁,还有其他可怕的暴行。
在那段时期,中国人并非日本暴行的唯一受害者。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从1932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日本从各地绑架并引诱大量女性,其中最著名的是当时的日本殖民地朝鲜,并将她们关押在被称为“慰安所”的妓院里,这些妓院以性奴役为由,为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务”。这些慰安所的受害者人数超过20万,而那些反抗的女性则遭到强奸、殴打,甚至可能被谋杀。
这些事实向我们讲述了20世纪殖民史上最残酷、最被遗忘的一页。虽然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欧洲军队犯下的事件和暴行上,但当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扩张到包括现在的台湾、韩国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之后,日本殖民主义的记忆,包括生物实验、性奴役、可怕的酷刑、强迫劳动和大屠杀,却常常被忽视。近乎完全孤立了两个世纪的日本,是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变成这个嗜血的帝国主义怪物的?它又是如何同时敌视西方并接受其思想和愿景的?
俄罗斯、美国、鸦片:日本为何考虑扩张?
马修·博农(Mathew Bonnon)在其学术论文《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种自卫机制》(Japanese Imperialism as a Self Defence Mechanism)中指出,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日本转向帝国主义和扩张,主要是由于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对西方敌人的恐惧。直到19世纪下半叶,我们所知的日本才真正存在。当时的日本是由分散、脱节的社会组成的,居住在一系列相邻的岛屿上,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和语言差异。
这些社会受制于德川幕府的政治体制,该体制持续了约260年(1603-1863年)。其核心思想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京都的天皇仅仅是象征性的统治者,代表着宗教的合法性,却不拥有行政权力。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著名的明治维新(1868年)。明治维新将中央权力交还天皇,废除了封建统治。取而代之的是,明治维新开创了一种新型的中央集权政府,开启了“现代化时代”。与此同时,日本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政府也开始传播民族主义意识以及身为日本人的深刻意义。
然而,19世纪末,日本才刚刚开启现代化进程,重新定义自身,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一方面,俄罗斯帝国向东扩张,势力范围延伸至附近的萨哈林岛,并迫使日本向其敞开贸易大门。另一方面,日本人则目睹了欧洲列强在中国向民众传播鸦片时的所作所为。他们目睹了法国和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中国人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以及他们如何迫使中国给予他们广泛的贸易优惠。此外,日本还将目光锁定在了美国身上,而美国正向西扩张,势力日益强大,给这个新兴的亚洲国家带来了诸多担忧。
在这些不确定的形势下,随着明治维新和日本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新兴帝国于1871年至1873年间派遣了其最著名的远征队——岩仓使团,前往欧洲和美国。岩仓使团以其领队岩仓具的名字命名,岩仓具是明治维新最杰出的缔造者之一。使团由约50名成员(后来成为日本的新精英)和50名学生组成,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市,认真学习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工业、教育、宗教、交通、通讯、文化和娱乐。他们还与国王、总理、商界领袖和顶尖学者进行了磋商。
日本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学习西方的经验、制度以及政治、工业、军事和教育思想,并试图效仿。这支使团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结论是,日本应该专注于建立先进的教育体系、正规军、富足的经济,以及由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撑的国家认同。这意味着日本似乎必须兼顾两个对立面:对西方扩张至周边地区的恐惧,以及同时进行西方式现代化的渴望。
这种奇特的地缘政治考量与现代化带来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结合,迅速在日本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扩张欲望。学者马修·博农认为,对被殖民的强烈恐惧促使日本帝国迅速向既有帝国学习,并发展出自我保护的手段。因此,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帝国主义的兴起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明治维新后,日本内外政策发生巨变,与此同时,日本不得不适应一个更为广泛的世界秩序,其核心理念是“强者必须扩张,否则将被吞并”。这种理念源于西方,同时也源于日本自身对西方的恐惧,驱使它通过地理扩张重新发现自我,力图成为与西方殖民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因此,日本迅速于1895年占领台湾,1910年吞并朝鲜,踏上了成为西方式东亚殖民强国的雄心勃勃的征程。
鉴于此,马修·博农认为,日本帝国扩张主要是出于“心理原因”。当时,日本认为,一个不向外扩张的国家不会受到尊重。因此,将朝鲜和台湾置于日本的中央集权之下,是展示日本实力并赢得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尊重的一种方式,这样其他列强在入侵日本之前就必须三思而后行。
简而言之,日本对赢得西方尊重的执着在其帝国主义情绪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从西方世界获得的认可,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之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渴望。随着在亚洲的连连胜利、西方对其实力的认可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日本开始将西方的知识视野内化于其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之中。它开始将自己视为原始人丛林中的文明中心。
日本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战胜俄国,这不仅提升了西方对日本崛起的关注,也强化了西方对日本的认同感,认为日本是一个摆脱“亚洲愚昧的枷锁”、迈向现代化和发展的世界强国。在亲眼目睹了自己在这场独特的事件中战胜了白人强国俄国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相对安全,不再受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
此外,这场胜利还鼓舞了许多其他尚未遭受日本占领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并认为日本应是亚洲大陆的天然霸主。后来,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行列,得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它获得了先前被德国殖民的领土,包括中国山东省的青岛,以及太平洋上原由德国控制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日本随后开始享受其在大国俱乐部中稳固的地位,并开始专注于国内增长,并将经济自由主义视为发展的法宝。然而,它再次与传统的殖民国家发生冲突,这些国家当场关闭了贸易大门,并保护其殖民地市场免受日本商品的侵害。这让日本意识到,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自由市场不过是一场幻觉。这甚至发展到根据20世纪20年代的反亚洲移民法,关闭了日本人向西方移民的大门。因此,日本越来越相信,世界和平和国际联盟的理念不过是幻想,当它们服务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时,它们就会被宣扬;当它们服务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它们就会被遗忘。
面对这些现实,日本于1931年通过进攻满洲重新定义了其在亚洲的扩张主义政策。此举旨在打开日本经济的大门,尤其是在日本原材料匮乏、西方通往日本的贸易路线封闭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到1936年初,日本已完全从军事角度思考问题,其军事机构如今拥有巨大的权力,对文官内阁行使主权,并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否决权”。
研究员兼作家、《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一书的作者堀田江理(Eri Hotta)总结了这一时期日本日益高涨的帝国主义情绪,她认为,对日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机会,使这个亚洲帝国相信其扩张步伐不可避免,是大东亚和新亚洲秩序共同繁荣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人开始赋予扩张主义以宗教色彩。正如他们坚信天皇是神圣的象征一样,他们也相信控制东南亚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日本人认为对抗西方不仅对日本自身利益至关重要,也对确保整个亚洲的稳定至关重要。这种情绪在1941年末达到顶峰,当时日本选择以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加强与纳粹德国的联盟来回应美国的升级举措,例如切断钢铁和航空燃料的运输。
这些升级的举措导致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美国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也被切断。反过来,日本开始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并最终导致日本派遣六艘航空母舰上的353架飞机编队前往海上,试图摧毁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基地。这促使美国在二战期间正式加入盟军护航队。
南进论:成为刽子手的受害者
自明治初期以来,日本便有两项基本政治战略,即“南进论”(向南推进)和“北进论”(向北推进)。尽管这两个术语都带有扩张主义的色彩,但它们最初的含义主要围绕贸易,尤其是“南进论”,指的是扩大与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以及南北美洲的贸易。然而,随着各种因素的汇聚,促使日本走向帝国主义,这两个术语很快便被赋予了更强的军事含义。
日本在19世纪摆脱了殖民统治,并通过改革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其实力丝毫不逊于西方殖民列强,并且稳步发展。随着这一发展,日本开始构建其在亚洲角色的新理念。这一角色是“将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他们摆脱落后走向发展,赶超日本”。如此一来,亚洲将成为“亚洲人的土地”。
在这一框架下,日本主张将中国从西方支持的政权中解放出来,将马来西亚和缅甸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将印度支那从法国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将菲律宾从美国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然而,研究员堀田江理认为,“南进论”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肩负神圣责任,将亚洲兄弟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引导他们走上进步道路的信念,很快就变成了对这些亚洲地区进行经济剥削的理论,而不是解放他们的理论。她认为,此事类似于美国白人定居者对美国原住民的所作所为,他们以神圣使命的名义被杀害和折磨。
根据一篇题为《导论:明治时代日本的种族与帝国》(Introduction: Race and Empire in Meiji Japan)的研究论文,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西方关于等级制度、科学、文化和种族等基本概念的内化。随后,日本国内的种族主义话语愈演愈烈,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日本越来越坚信欧洲是值得效仿的典范,而其他亚洲文化尽管高喊着解放亚洲的口号,却依然显得原始而失败。
当时,媒体在宣传先进日本原住民与居住在日本占领区的原始民族之间存在巨大文化差异这一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治政府官员甚至呼吁消灭日本周边地区那些他们认为落后的原始民族,就像日本对伊豆半岛(今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日本北部原住民之一)所做的那样。
在台湾岛、琉球群岛、萨哈林岛,甚至朝鲜半岛,日本政府都试图履行其所谓的“启蒙”使命:用日本文化和价值观教育这些地区的人民。简而言之,日本将邻国视为无助的生物,需要汲取一些日本的启蒙思想,以摆脱原始和无助的状态。
日本的进步伴随着种族和族裔话语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主导地位,并渗透到科学、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日本的崛起在西方被视为一个奇迹,因为这个不属于白种人的“黄种人”能够达到与西方相当的发展水平,并且——根据西方种族主义话语——能够摆脱周边种族落后的阴影。
事实上,即使在日本对西方抱有敌意、试图阻止其扩张并与之正面交锋时,日本也充斥着这种话语,并将这种观念内化。因此,它实际上将自己视为亚洲其他民族中的一个例外,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有助于理解日本如何成为其周边亚洲人的迫害者,以及如何卷入针对大陆上大量周边民族的极端暴力行为,尽管其扩张主义的借口是解放亚洲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
你的反应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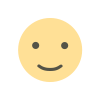 喜欢
0
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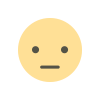 不喜欢
0
不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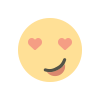 喜爱
0
喜爱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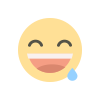 有趣
0
有趣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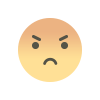 愤怒
0
愤怒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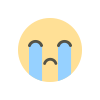 悲伤
0
悲伤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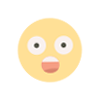 哇
0
哇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