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东冲突与冷战的回归

中东地区似乎正经历着一种令人联想起冷战时代的氛围——中美两国在这个正在经历重大变革的动荡地区日益争夺影响力。尽管中国在传统上关注的是贸易和能源资源获取,但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中国的中东政策正在发生转变,尤其是在今年6月的伊朗-以色列冲突之后。
与美国的传统观点相反,中方寻求确保其投资和伊朗石油的供应,这促使其加强与伊朗之间的安全和军事联系。这种转变不同于中方一贯的中立立场,并证实了其保护自身战略利益的愿望,而这些利益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高度相交。
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代理人战争”的场景在多个领域内反复上演,例如也门战场以及基于重大利益而对当地势力提供支持。中国对伊朗的政策与其对其他行为主体的态度不同,因为伊朗政权的存在和稳定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对中方至关重要。相比之下,美国则寻求维护其传统盟友的安全,并保持有效的军事存在以确保地区平衡。
在此背景下,作者史蒂文·库克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这些发展,并在其中描绘了中东冲突的新图景:国际和地区大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其结果难以预测,发生错误和结盟政策的代价也随之上升。因此,世界正面临着一种令人联想起冷战战术的局面,但其形式更加现代化,其挑战也更加复杂和危险。
正文:
去年春天,我有幸前往中国香港地区。我在那里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士,并讨论了美中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在谈到中东问题时,我的一位对话者转达道,中方对该地区的看法与美国不同,他宣称:“我们只想在中东买卖东西。仅此而已。” 多年来,许多西方的中国事务分析人士都使用类似的措辞来描述中国的政策,但我怀疑中国对该地区的态度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自今年6月底以色列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以来,有几份报道详细描述了中方帮助伊朗重建军事能力的努力。如果消息属实,那么这些举措将代表中方对中东冲突保持中立的立场发生的重大转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我还没准备好翻出我的换季衣物,而中东就似乎已在酝酿一场类似20世纪80年代中期冷战时代的代理人冲突。美国和以色列曾让伊朗血流成河。为了保护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显然认为必须帮助伊朗政权重建军事能力。任何熟悉美苏关系史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种动态不太可能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围绕着我在香港地区时听到的那句当务之急:向该地区出售商品,也从该地区购买商品(主要是能源)。这意味着中方希望该地区保持稳定、能源资源的自由流动、航行自由和市场准入。
这些条件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重叠,但中美两国非但没有合作,反而陷入了战略竞争。这与中东关系不大,而是关系到台海问题、被中方视为势力范围的亚洲地区,以及一个守成大国和一个希望改变全球秩序以使之对自身有利的新兴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
但是这种竞争体现在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地——中美双方不断在那里试图智胜对方。
也门和胡塞武装就是这场竞争如何展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中国和美国在确保航行自由方面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但二者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构成的挑战。中方基本上与胡塞武装达成了一项协议,以保护中国的航运线路免受攻击。而美国则动用军事力量以迫使胡塞武装撤退(结果好坏参半)。这对中方来说是一出完美的表演。美国因打击胡塞武装而在全球舆论中受到打击,而原本可能部署在亚洲的美国军事资源则被困在中东地区。此外,中国军方利用其在吉布提的基地来仔细监察美国海军的运作方式——这在台海地区爆发冲突时可能会派上用场。
在2023年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之后,中国还利用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从而不仅在中东,还在整个全球南方地区都获得了优势。文章称,中方一直非同寻常地批评以色列,但其强硬语气似乎与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关系不大,而是为了将美国与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全球声誉。
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并加大反以言论的力度,是中国决策者让美国决策者头疼的一种低成本手段。这似乎与他们对伊朗的态度截然不同,而中方实际上需要伊朗。中国政府可以应对没有胡塞武装或批评以色列的情况,但它无法轻易取代从德黑兰进口的约13%的石油。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24年的进口量为平均每天1110万桶)而言,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如此重视伊朗稳定的原因。在2021年,两国外长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尽管协议的最终版本从未公开,但是根据《纽约时报》获得的一份草案,其内容要求中国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以换取伊朗持续大幅供应折扣石油。尽管中方轻松获取能源资源是该协议的核心,但该草案也包含了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加强双方国防和安全合作的条款。
然而,即使最终协议与草案内容存在分歧,但仅凭石油贸易就表明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比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的都更为紧密。正因如此,与那些克制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对以色列进行反思性批评的人的看法相反,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在今年6月的战争并未让中方受益。
以色列技术先进、执行精良的军事行动——再加上美国对伊朗3处核设施的空袭,从两个层面打击了中方的利益:首先,它似乎强化了由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近年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采取措施以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这种缩减促使中东地区领导人亲近中国和俄罗斯。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午夜之锤”行动表明,美国认真对待该地区国家(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这巩固了此前因该地区担心美国“重返亚洲”将使其合作伙伴受制于伊朗而显得摇摇欲坠的主导秩序。但美国展现决心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终结。该地区领导人喜欢与中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又倾向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而非任何其他选择。
其次,以色列严重损害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及其政权的镇压手段。如今的伊朗比6月13日之前更加虚弱。一个虚弱且可能不稳定的伊朗将在经济和地缘战略上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损害。中国明智地囤积石油,但即使是石油供应的暂时中断,也可能会对中国(以及所有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伊朗伊斯兰政权垮台,一个对美国更加友好的新领导人上台,这可能会削弱中方在该地区制衡华盛顿的能力,甚至使之陷入困境。因此,中方迅速采取行动重建伊朗的防空能力及其弹道导弹库存,这是合情合理之举。
对于我们这些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东问题的人而言,这也像是一场地区战略博弈的一部分。1967年,当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惊人胜利后,苏联迅速重建了埃及军队。以色列在那场冲突中击败了莫斯科的盟友,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一场胜利。在近60年后,类似的激励和压力似乎正在塑造美国、以色列、伊朗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关系。特朗普政府致力于确保以色列拥有应对其安全威胁所需的资源,包括来自伊朗的威胁。同样,中国也在帮助伊朗减轻来自以色列的威胁。如果以色列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这一过程可能还会重演,并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本已相当重要的地区斗争。冷战时期的情况大致如此。
这种类比远非完美。与上世纪80年代的萨尔瓦多相比,以色列不像是一个附庸国。以色列同时还与中国保持着稳固的经济关系,而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合作伙伴通常没有这种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很难不再次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氛围——当时,在超级大国竞争的层面之下,零和冲突盛行,世界还要危险得多。
你的反应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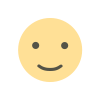 喜欢
0
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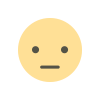 不喜欢
0
不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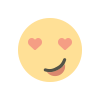 喜爱
0
喜爱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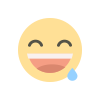 有趣
0
有趣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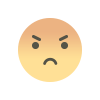 愤怒
0
愤怒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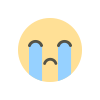 悲伤
0
悲伤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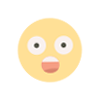 哇
0
哇
0











